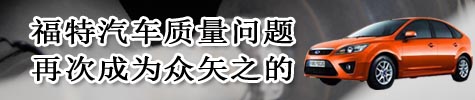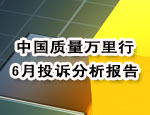“中國市場就是這樣,誰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睜眼會發(fā)生什么,但我終于不用每天擔心這些了。”寶馬大中華區(qū)總裁史登科在臨別之際發(fā)出了這樣的感慨。
過去半年,大眾汽車集團(中國)總裁兼CEO倪凱銘、戴姆勒東北亞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華立新、寶馬集團大中華區(qū)總裁兼CEO史登科接連去職。對于他們個人而言,離開競爭日益激烈、壓力倍增的中國市場或許是一種解脫。但對于中國汽車市場而言,這無異于一次“地震”。
三大德國車企要干什么?“集體換防”似乎不是巧合!一時間,外界對這次人事風波的各種猜測沸沸揚揚。
流言四起
第一個離開的是大眾中國總裁倪凱銘。
“倪凱銘離開大眾中國的導火索是年初的DSG變速器事件。”9月底的巴黎車展,同行的一位媒體人這樣向汽車商報記者表示,“倪凱銘沒有處理好這件事,大眾汽車集團CEO文德恩對此頗為不滿。對于大眾來說,DSG事件損失的不僅僅是幾億歐元,更讓大眾在中國市場上遭受了一次信譽危機。”
如果說倪凱銘的走還有些許先兆,那么華立新與史登科的離去則讓許多業(yè)內(nèi)人士感到疑惑。12月23日,一位知情人士向汽車商報記者獨家透露,戴姆勒東北亞董事長華立新本已在任期將滿前續(xù)約并確定出任奔馳中國與北京奔馳共同成立的銷售公司董事長一職。作為奔馳渠道整合的主推人之一,大功告成卻突然離任,實在令人捉摸不透。史登科的“提前退休”同樣令人不解。雖然已經(jīng)在任8年,但58歲的“老史”尚未到退休年齡。更重要的是,“華立新與史登科在中國順風順水、功勛卓著,為什么在這個節(jié)骨眼兒上離職?”
12月末,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業(yè)內(nèi)人士對記者表示,三大德國企業(yè)“集體換防”顯然不是因為業(yè)績不好、領導引咎辭職,反而可能是業(yè)績太好,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,所以德國總部更加重視這塊市場,要親自過問了。
數(shù)據(jù)顯示,南北兩個大眾2012年總銷量逼近250萬輛,創(chuàng)歷史新高。以今年大眾全球銷量維持去年800萬輛計算,中國已經(jīng)占其總銷量超過四分之一;寶馬今年也保持高速增長,前11個月銷量已突破30萬輛,占全球總銷量近20%;奔馳前11個月實現(xiàn)銷量約18萬輛,全球比重也達到約15%。
面對中國市場分量的快速上升,德國總部關注的增加似乎不難理解。但前述人士口中的“親自過問”究竟意味著什么?從12月末流行于媒體和微博上的言論看,不少人把它理解為德國總部要收權。
事實是否真的如此?
12月24日,記者分別致電大眾中國、戴姆勒東北亞以及寶馬大中華區(qū)相關部門,但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一致地拒絕對此事發(fā)表評論。
收還是放?
“收權,或者說把最重要的市場看緊一點,似乎是人之常情。”12月22日,一位行業(yè)研究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,“但是,無論從三大德國企業(yè)在中國的歷史還是中國汽車市場的內(nèi)在要求上看,它們過去其實一直是在逐漸親近中國、給中國市場更多的自由度。一朝逆轉(zhuǎn)很難解釋得通。”
“不少汽車企業(yè)的亞太總部原本都設在香港、新加坡,它們經(jīng)歷了一個逐步進入中國的過程,奔馳是一個典型”。前述行業(yè)研究者對記者表示。公開資料顯示,1986年,奔馳牽手香港本地公司利星行,在香港成立梅賽德斯-奔馳(中國)有限公司。9年后的2005年,北京奔馳-戴姆勒·克萊斯勒汽車有限公司成立,但奔馳中國業(yè)務的中樞依然在香港。直到2006年,梅賽德斯-奔馳中國總部才遷至北京,同時更名為梅賽德斯-奔馳(中國)汽車銷售有限公司。大眾和寶馬在中國境內(nèi)成立類似的機構也經(jīng)歷了漫長過程。盡管上世紀80年代初就有了上海大眾,但大眾中國卻在1999年才成立,而寶馬的中國辦事處成立于1994年,直到2005年才成立了寶馬大中華區(qū)。
“德國企業(yè)剛來的時候,有些固執(zhí),把自己的話語權看的很重。”12月21日,一位曾工作于上海大眾的老員工對記者說,“中國人更改一顆螺絲都要經(jīng)過德國人批準的著名段子就是出自那個時期,但隨著中國市場的爆發(fā),以及中國人‘地利’優(yōu)勢越來越重要,德國人也開始松動。”
2008年中國車市進入高潮期之后,這種松動愈演愈烈。在上海大眾,中國人參與了朗逸車型的原始開發(fā);在華晨寶馬,寶馬甚至愿意把老款5系的平臺轉(zhuǎn)讓給對方;奔馳中國則為了與北京奔馳實現(xiàn)融合,甚至“勸退”了多年的伙伴利星行。
“無論是大眾中國曾經(jīng)的總裁范安德還是華立新、史登科,中國市場的分量和汽車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展要求都迫使他們相信,只有加速本土化、現(xiàn)地化才能有出路,同時只有理解中國、適應中國市場,給它最大限度的靈活性,才能成功”前文提及的行業(yè)研究者說:“這是雙方磨合、妥協(xié)的結(jié)果,但更是必然的理性選擇。盡管期間難免有沖突和波折。”
12月25日,一位已經(jīng)離職的奔馳中國前高級經(jīng)理人對記者表示,多年前,奔馳中國向德國總部申請某款暢銷進口車,但常常不能按照提出的數(shù)量、配置和顏色拿到車,造成了市場的被動。“那時候,總部還是有些‘官老爺’習氣,現(xiàn)在不可能了。從其它地方調(diào),也要先滿足中國。”而曾經(jīng)和史登科共事的一位前寶馬大中華區(qū)員工也對記者表示,為了說服德國總部,老史常常著急搓火。
史登科離任之后,不少國內(nèi)外媒體評論他“跨國公司經(jīng)理人融入中國的典范”,無疑他的業(yè)績和處事方式得到了中德雙方的一致認可。既然適應中國、理解中國并為中國區(qū)爭取話語權的史登科是成功的范本,德國企業(yè)豈會反其道而行之?“集體換防”或有它意?
布局
據(jù)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報道,得益于中國市場的強勁推動,大眾集團2011年全球稅前總利潤達189億歐元。其中,中國市場實現(xiàn)利潤77億歐元,占集團利潤總額的40%。同樣是在2011年,由于中國市場的拉動,奧迪在全球豪華車品牌銷量的競爭中超越奔馳,也將自己與寶馬的差距縮小到8萬輛。“得中國者得天下”對德國汽車品牌來說已經(jīng)是至理名言。
“布局!一切都是為了面向新的競爭而布局。”12月24日,一位市場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,“過去10年,奧迪、寶馬和奔馳其實只是完成了在中國市場上的初步鋪開,未來10年才是大展拳腳的時候。”
該人士認為,過去10年三大豪華品牌實現(xiàn)了兩大目標。第一,在中國找到本土合作伙伴實現(xiàn)本地生產(chǎn);第二,重新塑造在中國的品牌形象。他舉例稱,無論是奧迪的年輕化戰(zhàn)略、寶馬的“悅”還是奔馳的“品牌回歸”計劃,都是典型的品牌塑造期行為。隨著市場開拓的深化,它們之間的競爭格局也要發(fā)生變化。
諸多跡象表明,競爭格局正在變化。2012年,中國豪華車市場罕見地出現(xiàn)了短暫的價格戰(zhàn)。業(yè)內(nèi)人士認為,這表明豪華車市場已經(jīng)從過去的單一品牌力較量轉(zhuǎn)為更充分的全面較量,價格、服務、網(wǎng)絡等市場青春期并不顯眼的要素開始逐一對撞。從另一個角度看,中國消費者正在經(jīng)歷豪華車“除魅”的階段,他們對豪華車的要求會越來越細致,汽車企業(yè)必須在每個環(huán)節(jié)做得最好。
“必須注意到,戴姆勒東北亞投資有限公司即將上任的新董事長Hubertus Troska、寶馬大中華區(qū)接替史登科的安格無不是在其它單一市場有過全產(chǎn)業(yè)鏈完整經(jīng)驗的資深人士。相比華立新、史登科這樣的開拓型‘闖將’,他們的經(jīng)驗更為全面,也更能適應中國市場競爭層次的細化。”前述市場分析人士認為,“這也從側(cè)面證明,三大德國車企,已經(jīng)在為未來的全面競爭、細分競爭做準備。”
“中國最好的10年已經(jīng)過去,今后問題會越來越多,因為競爭越來越激烈,情況越來越復雜。”史登科的話是總結(jié),或許也是對未來“三大”接班人們的提點。
這些“新人”真的會“蕭規(guī)曹隨”?他們能否將三大品牌進行當中的本土化戰(zhàn)略堅持下去?“已經(jīng)從中國市場過去幾年發(fā)展嘗到甜頭的‘大老板’們——戴姆勒集團及梅賽德斯-奔馳CEO蔡澈、大眾汽車CEO文德恩、寶馬集團董事長雷瑟夫——我相信,他們會做出聰明的選擇。”前文提及的資深媒體人對記者說。